诵阅人偶
影片:假人,Golem(1980,波兰) 导演:亚当·艾略特
人们悲鸟之血,却无视鱼之伤,有声音的东西是幸福的。如果人偶们也有声音,大概会大叫,不想变成人类吧。——《攻壳机动队2》
Golem原词为גלמי,本意是“原料”,“胚胎”或“未成之人”,往往智能低下,接收指令后便会持续执行。
倒吊之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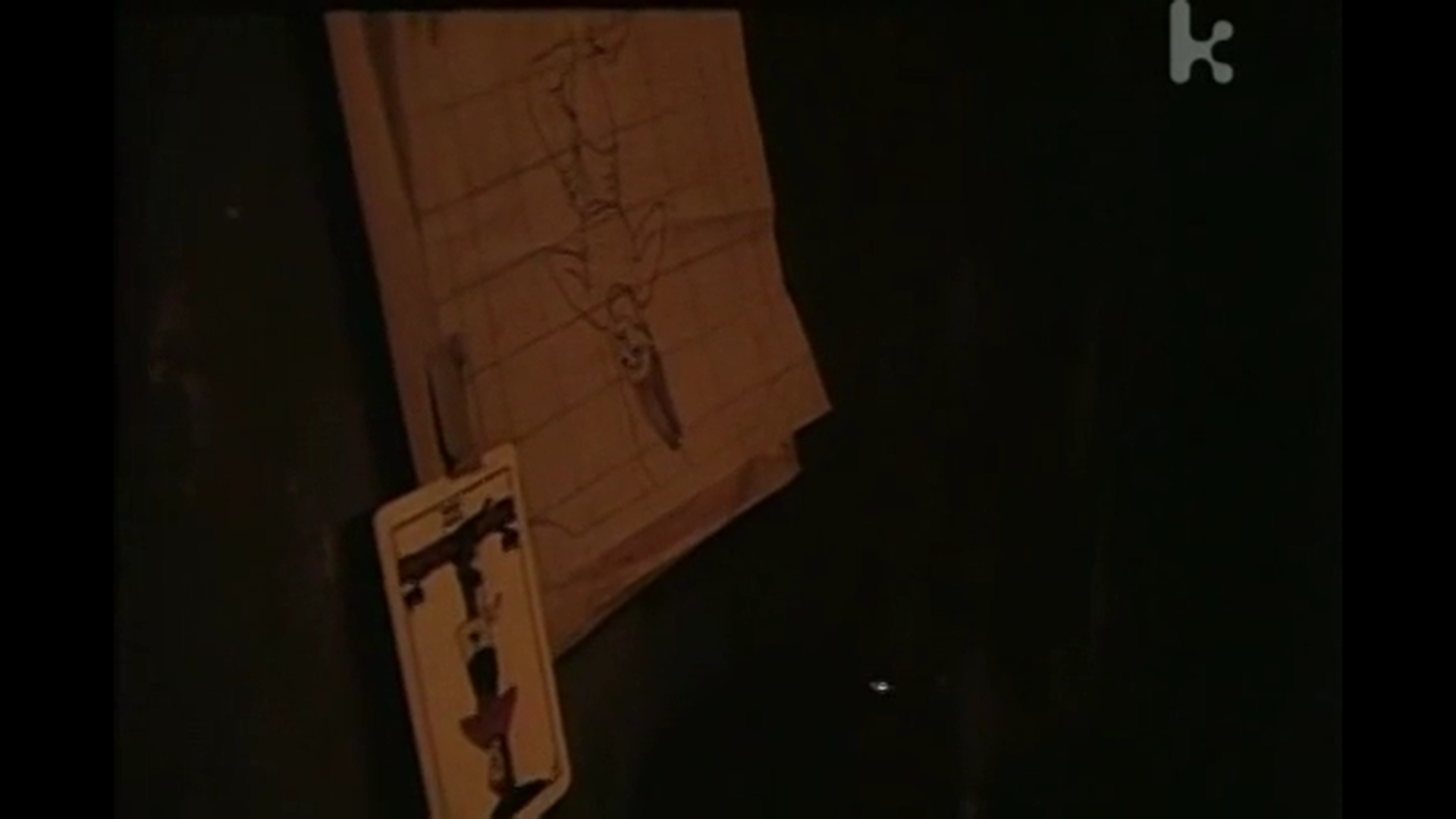
男子面容平静,双手反绑,倒着吊在“T”字型的树上。
牺牲、新的观点、悬挂、因循守旧,这些是这张倒吊人塔罗牌的寓意。
主人公普特纳就是该片的“倒吊之人”。
他从一项主题为优化人类的实验中诞生,在“原型”普特纳接受盘问“意外”死去后,他接替了遗留的大衣,哪怕他直言这并不是他的大衣。
研究者确信这个出逃的实验体已被排除,存在下来的是切实的“人”。
这位人偶便被迫披上了人的大衣,进入了人群中。
灰黄的光影,摇晃的镜头,开合的窗户,稀少的人群,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破败的城市光景,楼房仅仅是立在那边就已摇摇欲坠。
在这里,警民关系高压,妓女接待盲人,影院成为宗教场所,甚至乐团也并不和谐。
与灰败的环境相得益彰的是这里人们纯粹的民风,纯粹的不信任。
这使得普特纳于人的尊重和善意格格不入,他乐于聆听他人的意见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提供帮助,被问到为何如此时,他天真的回复常被人评价为“不存在于这个世界”,就像那些危楼一般无处落脚。
而他也不恼,仍旧从善,遇到死去的警长,会为他闭上双眼,就算这一举动会为他招致不必要的嫌疑。
普特纳的状态正如那张塔罗牌上的倒吊人被悬置。
他既超脱事外,又深陷其中,他的善意无法改变环境,却在不断的否定与孤立中显出一种异样的坚韧。
正是在这份“倒吊”的状态中,他成为了一个被认定的“人”。
萌芽新生

“新的生命要是萌芽,它的种子须是死的” ——《记忆的质料》
普特纳被认定为“人”是实验者的意外收获,一具空壳若是“骗过”了真实的人,它的一切便都具有了研究的意义,实验者们也就默认了普特纳的存在。
而对于普特纳来说,“过去”形成养料仅仅提供了一个脆弱的落点,让他能够有一个不那么突兀的身份存在于群体中。
实验者同“上层”被刻意隐去,留下“更好的人”这一命题,“心地善良”或许是普特纳的初始设定,但在一个暴力与猜忌主导的世界里,连最简单的善意都被视为可疑。
管理员得知普特纳愿意借钱给自己,一度认为女儿为了钱而卖淫。
“这本书对你肯定有帮助。”
误会解开后,管理员这样认定,乐呵地要去拿回他未成的作品与他分享。
至此住户名单上的两个“普特纳”对于他来说,也从一种麻烦转变为了别的什么。
这或许是导演留有的一点温暖,至少可见善意推动了一点善意,即便微弱,也仍是新生。
两位普特纳,一位从人化为仅剩名字的空壳,另一位从仅有名字的空壳化为人。
新生命的种子,正是早已死去的。
笼中之鼠

当我游荡在黑暗的街头,我在那里能找到的最后陌路上,其实是在寻觅一种方式,想在保持智识自由的同时,让自己的情感也再次归属于人群。——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
实验一词透露着理性与中立,而对于小白鼠而言,或许并不一定。
小白鼠作为明示的线索之一,于开篇便出现,成群的白鼠挤占着画面蠕动着,像是传递给观众一种信息:这场实验已被重复无数次。
在种子长成稻时,小白鼠散落在屋内走动着,此时普特纳拥有了足够的认可去成为人,普特纳和小白鼠都从笼中逃离了……吗?
随风开开合合的窗曾令人不寒而栗,再向那堵墙望去,窗户已不再,只留下空洞的窗孔,是时移事迁?还是另有隐情。
他在遥望时,是「人」吗?
普特纳在他成为人的路上,只停留在这个群体。
笔者从未使用“社会”或“城市”,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尽显病态,很难说这些人有互相影响着;二是人员体量太小,完全达不到形成一个“城市”的规模。
或许普特纳从始至终都只是从一个“出生”的实验箱转移到一个“成为人”的实验箱,这第二个实验箱里的所有个体,也都只是小白鼠。
而后,普特纳加入了要为政府吹奏的乐队,随着人群向着模糊的前方小跑。
片末,一位戴着眼镜的发言人宣讲着政府的可靠,呼吁民众不要相信有关新人类的言论。
这个男人手上拿着普特纳的号码牌,形似普特纳,但他会是我们一直看过来的那个普特纳吗?
或许这位人偶的存在仅是翻阅诵读人们对「人」的期许。
在这些不确定性中,只留下:何意味?
